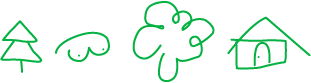書評:人造地獄──參與式藝術與觀看者政治
文|吳礽喻
如果世界是一個房間,藝術界的大小大概就是一個鞋盒,在鞋盒裡的百百種微生態系裡,「參與式」藝術是近年來最火熱的一門,但主要的問題是,在社群網路的世代裡,群眾募資、派對活動、公投公審,什麼不是在號招眾人參與;電視、網路上的整人節目,設定一個情境融入生活場景,看看能激起誤入陷阱的民眾有什麼樣的反應……當代的藝術家就算再挑釁、前衛、打破藝術與社會的疆野,依然在這有限的鞋盒裡,依附在政府補助的雙年展、藝術節、駐村計畫、社區營造專案,夢想著執行「更具社會性、更協作、比藝術更真實」有用的作品。也淪為新自由主義下,派遣勞工的典型:社區藝術家的定位漸漸「不再是運動者,而是某個國家機構的臨時僱員。我們讓國家的一個部門派一群人去收拾另一個國家部門留下的爛攤子,卻否認我們是為國家工作。」(原文p.185、譯本p.315)而藝術評論者也缺少歷史、文化政治的脈絡去評斷許許多多以「人和群眾」為主要媒材的創作,導致類似的情境、作品或問題不斷重演、不相銜接,落入窠臼和鬼打牆的狀態,既無法回應參與式藝術和其他新興網路媒體、社會政治操作的差異,也無法幫助體制對藝術家的利用和剝削狀態。無法被超渡,無法去投胎,有沒有一種誤入地獄感?
跟著Claire Bishop追溯不同國家政權、歷史脈絡的噠噠馬蹄聲,無論你是落在「熱衷於參與與協作藝術」、「憑什麼要求我參與你的藝術?」或「參與式藝術可以吃嗎?」光譜上任何一點的人,她都提出了豐富、有趣的案例顛覆既有印象、激發思考:從二戰前的歐洲,未來派號招民眾參與的藝術「晚宴」、劇場、各大都市巡迴、街頭活動,藉此在義大利推廣好戰的法西斯民粹主義,這樣你還會覺得由藝術家來帶領社區營造、民眾參與都旨在良善意圖?1917年俄國無產階級運動,激進音樂家號招把所有象徵資產階級的鋼琴都丟掉,1922年慶祝大會上用火車的汽笛、工廠的噪音創作屬於無產階級的集體交響樂!本書名取自1920年代布赫東(Andre Breton)參與達達主義一連串遊街活動後寫的文章,達達主義訴求孩童般的無厘頭,但每項活動卻是精心策劃,查拉(Tristan Tzara)善於媒體操作,用卓別林將蒞臨講演當做走讀活動的賣點,但來參與達達活動的觀眾的期待更大,希望目睹造反、醜聞,只是遊街導覽讓許多人興味索然,導致布赫東寫道「一個成功的人,或者再也沒有人要攻擊他的人,是個死人。」這樣的落差,是否和現在許多具有政治訴求的作品相仿,讓人覺得「參與了,然後呢?」
對,活動結束後也要發個新聞稿──我們會發現有些之後的藝術行動更高明,有時活動本身也是假的,只是一些事先安排好的照片,就可以發活動結束的新聞稿了。
接下來帶出五、六零年代在法國為了反抗消費主義「異化」主體性的爭論,而衍生出主流藝術史顯少著墨的「情境主義」、「視覺藝術研究社」、「樂貝爾偶發藝術」大混戰,只是在這個當/現代藝術的鞋盒裡,沒有一個屬於亞洲參與式藝術的參考座標,有南美洲的,巴西導演奧古斯托.波瓦(Augusto Boal)的「隱形劇場」,曾在一個餐廳裡安插演員,讓大家目睹一個吃了霸王餐的情節,又讓民眾討論勞動薪資不平均的問題,當場成功募資為主事者解圍,避開獨裁政權審查演了一齣戲。而為了嘲諷「偶發藝術」媒體熱潮,因此號招其他藝術家一起發假新聞稿的,則是阿根廷的作家瑪索塔(Oscar Masotta)。
Claire Bishop在《人造地獄》採取的研究方法,是針砭過去二十年來美國社區藝術熱潮,特別跳過美國這一塊,用前蘇聯共產國家、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南美獨裁政權、英國70年代「藝企合作」、侵佔空屋式的社區藝術等範例,來拉開參與式藝術可以被討論的空間,以及面臨的種種問題。別再膠著於參與式藝術的理想性,「好人總是自以為是」般的做好事心態導致這些藝術計畫的衰竭與無疾而終、被政府收割、外包,轉化為可評鑑的KPI數據。而亞洲與台灣的參與式藝術,或許一開始就不在這個鞋盒裡,連跨國藝術體制高級皮鞋的鞋帶也做不成,頂多像是些散落塵螨般的存在,用顯微鏡才研究得出來,抑或在長成期間就被社會與政府吸乾精氣,在對社會、政治與群眾伸出稚嫩的爪牙之前就胎死腹中。所以不先收起這本葵花寶典和各式主義理論,乖乖地寫企劃書、履約、衝KPI,好好的做個生產者,還能怎麼做?不過說真的我恨透了接一再外包的案子,最後還要被稚嫩不安的政府外包商苛刻審查,台灣特有的問題和怪相或許可以獨立成為一個章節,讓我們讚頌那些姿態婉轉又能強硬的藝術家經紀人專案管理仲介,和政府官僚體制中的公務人員們,以西斯丁大教堂〈最後的審判〉風,裝飾在十八層地獄的門板上。